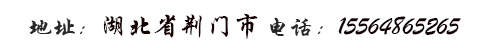话剧《冬之旅》剧评:《冬之旅》是暖的
|
看过了那么多戏,渐渐知道,戏与戏之间,好坏不在毫厘,而是差之千里的阻隔。成就是成,不成就是不成的。同时,我又明确地感受到有些东西比对技术的点评、对错的判断更重要,但又无法清晰地描述出来,直到那晚在舞台上看见那束光、那阵烟和那个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着,身影最终消失在侧幕不再见,才隐隐明白,对话剧艺术而言,创作的偏执、控制、情义、担当、坚持与坚持的对抗和进退、才华与才华的碰撞和厮磨,才是真正难和难得的。 那个老人是蓝天野。在全场所有的灯光设计里,那一个离场的渲染最为干净和萧索,一个简单的白色流动光从侧面射过来,烟雾升起,所有告别都悉数完成,所有怨恨都留在身后,他的戏演完了,要走了。那个背影走得稳健、释然,不快也不慢,已经演了1个小时又40分钟的疲惫都卸下了,已经演了60年的风霜都落满了衣衫。 这一切回到观者的眼里,都是幸。 剧本难免有拖冗的部分,舞美设计亦在结构上稍显繁复,空间多多少少被浪费了,还有那些忽而上忽而下的纱帘……但这些硬伤都在观看时被我自动地屏蔽掉了。也许,只有这样,我才能真的理解创作者在这方舞台上的所作所为,那股力量来自于何处,又为何终以此等风姿呈现出来。 因为是万方、赖声川、王可然、蓝天野、李立群的组合,还未踏入剧场半步,便已经本能地将作品划入不需要去甄辨和挑剔的范畴里了。纵使我袖子里藏了好多的刀,我眼睛里记挂再多的高,都不预备出手,不打算看穿。有一些戏可以审视、评说,有一些则必须聆听和敬畏。 故事离我们很遥远,未经历过那个动荡而血腥的岁月的我,不能准确无疑地知道“文革”二字的锋利和刺耳。一切若在身外,就只能揣测。那时一个年轻人没能给另一个年轻人打开自己的家门,他就要为自己的懦弱和犹疑付出整个后半生被记恨和不齿的代价,他就注定要在年迈的冬天里战战兢兢地敲开一扇门,佝偻着衰老的身体,一再低头认错。 此刻一个老人不接受另外一个老人的歉意和忏悔,他也势必要承受这怨恨带来的巨大的后坐力,直面生命中一块无法被吹散的阴郁始终盘踞在脑海里,并在有生之年一直为此困扰和折磨。 叶子长出新的又落下,落下之后会再长出新的。歌曲唱了一段停下了,按下播放键又继续唱下去。 爱恨情仇都是好说的事,最难抵抗的是无聊和失语、孤寂和遗忘,是一切还未开始你就开始怀疑,是戏都演完了可你还没醒来。冷漠并不能带来救赎,失去才会。 感谢编剧一言一语细密的织就,感谢长者们举重若轻的表演,感谢艺术和诗人,感谢凡人和佛陀,感谢这漫长的告别,让我甘愿放弃无谓的争论和躁动的自负,安静地感受大幕拉开那一刻:演员登台,内心简单的愉悦就像他们的衰老与和解一样,“就像麻雀说出黎明一样”。 冬天就要过去了,一个新的天堂即将卷土重来。.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aiwanzx.com/twls/1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“挖人”与“给台湾人才更好的价值”
- 下一篇文章: 周杰伦何来城堡童话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