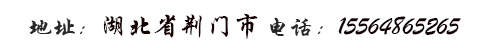赵刚台湾土狗力古道
|
赵刚现在大度山上下著冷雨,哪兒都去不了,來,你坐下,咱喝杯熱茶,我跟你說說力古道的事兒。 力古道在台灣原住民卑南族的話裡,就是「雲豹」的意思。雲豹是一種在台灣已滅絕的物種,好多年了,沒人在中央山脈或大武山脈裡看過牠的蹤跡,而那些高聳入雲的綠色山脈,曾經是一身美麗條紋的她出沒神隱之所在。力古道因為身上有著深淺不一的棕色條紋,而繼承了這個美麗的名字。 在台湾已经灭绝的云豹十一年前,我從頭目哈古那兒得到了這個名字。他說,黑的那隻叫Zhumai,花的那隻就叫Ligudao好了。在卑南語裡,Zhumai是台灣黑熊的意思。我後來給他們定了漢文音譯名字:力古道與竹麥。 有時我在宿舍區裡溜這兩條狗,遇到那些愛狗的,或是稍知狗市行情的,或只是想和我打招呼的人,他們常會說:「台灣土狗耶!」。我的老母親知道我從原住民那兒抱來兩隻小土狗,有點兒感慨繫之地和我說:「山地人的狗最厲害了,耳朵很靈,又忠心,又兇,日本人為了要征服山地人,把這些土狗屠殺了好多呢!」我不知道她是從哪兒聽來的這一段,但滿州國長大的她老人家的確對這一件「歷史事實」很上心,時常以好像是頭一次和我說的認真勁兒和我再說一次。最近她忘得更多了,這個檔案應該已經找不著了。 他們小的時候,出去散步我通常不給他們約束,我走在後頭,他們當我的開路先鋒,一左一右,搖著尾巴,聞著路邊的「野味兒」,一路歡歡而行。當其時,我總有點飄飄然,好像我的前世是高山族獵人似的。這時,我最怕有人煞風景,叫我趙老師。 就像我不是血統純正的漢人、蒙古人,或滿人,論血統,力古道和竹麥也不是那種所謂純種的,意思是有行情的,「台灣土狗」。但我覺得正好,雜種人與雜種狗,招搖過市,何需有行情。雖然我姓趙,但小時候我漢人母親常愛跟我說,你們家這個趙和漢人的趙姓沒有關係,是從肇事的那個「肇」字轉借過來的。所以啦,要說我不是「祖上趙家的」,其實也對。而若有好事者拿著百家姓說事兒,硬說我們的力古道是「趙家的狗」,那也是白搭。力古道就是力古道。 但力古道的確具有狗百科裡所記載的幾乎所有關於「台灣土狗」的特徵:中等身材,南瓜頭、杏仁眼、豹子腰、鐮刀尾、虎爪子,以及寬闊勇健的胸膛。在那個胸膛上,漂亮的毛髮分兩路從兩脅匯聚到前胸正中央,形成一道尖尖稜線,一路直達他的腹部…….。他胸前的毛髮是淺米色的,好像我早餐常吃的燕麥粥的那種顏色;可好看了!力古道喜歡在早上沾滿露水的草地上打滾,背向大地,面向藍天,沒完沒了地大面積使勁磨蹭他的背,眼睛因興奮而圓凸而閃著賊光,不時發出「呼嚕呼嚕」的愉快低鳴。草地是他的自助澡堂──我承認,我最多只幫他洗過兩三次澡。 台湾土狗唯一與狗百科上關於「台灣土狗」的特徵描述不一致的,是他的兩隻耳朵;他們不是豎尖的,而老是耷拉著──這是他祖輩的某一外族邂逅在他身上所銘刻的標誌吧。在那麼孔武矯健的身軀,以及「驍勇善戰,面對比牠大型的獵物也毫無懼意」(資料上如此說)的人格形象之上,配備著兩片兒好像店小二頭巾一樣滑稽的耳朵。 力古道是頭目的族人朋友,住在離部落不遠的公路旁山坡上的一對中年農民夫妻,送給我們的。那是一個晴朗的冬日,我們開車下去接牠們回台中,牠們一窩兄弟姊妹在暗暗的、逼庂的玉米田工寮裡,七八隻,各種顏色,我們選了兩隻,一黑一花。竹麥容易逮,一拎就起,力古道則是一看苗頭不對,機靈鑽到床底下,我們費了老大勁兒才把他給掏出來,他還一副不願就範的小苦惱模樣。他大概是懵懵懂懂地捨不得這一片青青山脈和那一片蔚藍太平洋吧!兩三年後,我在一次豐年祭裡,見到力古道和竹麥的生家,那個大嬸問小狗長得怎樣,跟我要照片,我答應了,卻到如今還失信著。我總是記著這筆債的,但問題是自從攝影數位化之後,我就幾乎沒洗過照片。唉,這也是藉口。數位革命對我沒好事,我美國的老師,老是在聖誕節的時候跟我要全家福,我答應歸答應但也一直沒寄,直到去年底才在女兒的協助下發出去了。到現在我還是不會用電腦發我相機裡的照片。 我們這個世界有太多愚人的故事了,還是說說力古道的睿智與英勇吧,至於他的弟弟竹麥,以後有時間再說。你問,為什麼力古道是哥哥?問得好,他非得是哥啊,哥是啥,哥就是那氣派,就是那作派。你就算讓竹麥當哥,他也當不了啊。 力古道是年底來到這個世界上的。到他遷居大度山之時,也不過兩三個月大,渾是一個毛肉球,但它長得飛快。過一個月,我們帶他去看獸醫時,他比竹麥就楞是大兩號。獸醫小伙子說,這隻花狗體型會比較大。問他何以知,他說,看牙齒唄。我問了很多問題,其中包括大度山眼鏡蛇多,狗和蛇若鬥起來怎辦?穿著有點髒髒的白袍子的獸醫小伙子,以一種「哈林」風的痞勁兒,簡潔地說:「nochance!」。不知怎地,這成了我的恆常擔心,因為我知道大肚山上有太多大猛狗被眼鏡蛇咬死,而對面的榮總,礙於什麼法不知道,就是不能提供血清給狗,於是很多條什麼黃金獵犬、拉不拉多、狼犬、杜賓,皆死於蛇吻之非命。 從小,基因裡只有大山大水的力古道就酷愛自由,然而,他卻幾乎一生皆在鎖鍊之中,這是後話。清晨,我把他和竹麥這對難兄難弟,從那因他倆的歡快而幾乎要跳起來的籠子裡放出來,於是他們就在近百坪的沾著露水的後院草地上玩你追我跑的遊戲,後院有坡,他倆簡直就是美國卡通裡的大野兔或小野狼,幾乎是帶著跑車尾氣與卡通配音般地極速奔跑、上坡下坡、急速煞車、直角轉彎,還會賊頭賊腦地作假動作……,那景觀真是美極了。有點兒像劉邦,我心裡話是:「今日方知養狗之樂也」。這倆傢伙在模擬田獵追逐的晨課之後,繼而在吃完早餐之後,就開始眼神閃爍、躡手躡腳地想溜出去。倆兄弟,一個是天龍,一個是地虎,竹麥靠刨地或是鑽圍籬的空隙,沒啥風格地硬擠出去,力古道,後來我們簡稱力古,則是超克圍籬,一兩個箭步上去,再一個鷂子翻身,唰地就到了圍籬之外。看得我目瞪口呆,不顧我的柔情與狠話齊飛,力古回眸一視,神情一如聶隱娘,情到深處如無情,絕然而行。為了自由,愛情誠可拋,可況人的愛信得過嗎? 从大肚山(亦作“大度山”)俯瞰台中市但是,至多一兩小時之後,我就聽到門口有動靜。可不是嗎,咱力古大寶回來了。有時還好,但常常是一身濕漉漉甚或渾身臭泥,不知跑到哪兒野去的。他奮力搖著尾巴,特別示好地,笑嘻嘻地,那意思似是,好啦,大人不記小人過嘛!我則是佯罵兩句,曲起中指指節,敲敲他的大腦門兒,「以後不准哪」。他抬頭看著我,目光純潔之至。 力古不是純「台灣土狗」,但他可土得緊吶!汽車、摩托車、腳踏車,娃娃車,什麼車都不敢坐。毛毛孩坐娃娃車,也是最近幾年出現的奇觀,有時我真想學耶穌在神殿裡踢翻那些放高利貸攤子的範兒,把帶進餐館的這種娃娃車給一腳踢到滿天雲兒裡……。怎說到這些洋娃娃了?還是說說咱土力古吧。力古一兩歲時候的一個春節,找不著人看顧他們,只好把他們載上台北,出發前,還到那個“nochance”獸醫那兒求了些鎮定劑,nochance說:上車前把藥灌進去,保證安靜到達目的地。但事實證明完全nochance,力古坐後座,一路瘋狂氣喘、極速心跳、雙眼紅通,正月也流火,在那兒扭啊哈啊叫啊,有一刻,我都覺得他要從後座把他已經卡在喉嚨的心臟,給吐到我後腦杓上了。還非得動員兩個人類女性的無比溫柔,這才把力古給安慰住,這才總算在高速路上沒出那可上有線電視台的亂子。那次我還真怕力古亂了性,把我們一車人等都給撕成碎片。後來是平安到了台北,但並非一夜無話。午夜凌晨開始的鞭炮聲,再度讓力古陷入大恐巨惴之中,直到天亮,他在小小庭院中不停遊走奔突,一如瘋虎在檻。那是力古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謂之「春節」的人類節日。 力古樂與人群,然性嗜自由。某日,他竟蹺家了。大概有個四五天吧,我到處找他,但沒想到逃犯竟然躲在警察局旁──就在離家不到五十米的樹林中的一個空宅旁的一個灌木叢裡,槁木死灰地、大島渚風格地,守著他女友,從灌木叢裡歉然地看著我;他當然認得我,但就是鐵了心腸不跟我走。我說槁木死灰,不只是他的眼神,一點兒光采都沒,好像在修道或是守墓,也是因為他身上的毛髮,因為好幾天沒吃飯,或是決絕傾注之故,似是抹了一層黑灰。力古!力古!我無效地叫了好幾聲,只有離開。過了兩天,他自己回來了,啥也沒說,日子照過。回想起來,那幾天,那個方向總是傳來狗群的激烈鬥爭聲。 力古看來是贏了那場擂台。報酬則是大度山上出現了他的後代。父子都是所謂虎斑,但子輩也混雜了牠們母親的基因,毛色比較淺、沒有腰身,也沒有鐮刀尾南瓜頭了。這些年來,每次牽著力古散步經過那個古戰場或是古愛場,他總是從喉嚨深處發出一種低低的哀鳴聲,但哼完兩聲,也就沒事了,繼續前行,了無罣礙,不像人啊,念念不斷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?著實神秘難解。 力古後來為何失去了自由,變成了「愛犬」,被獄卒趙某牽著放封呢?告訴你吧,因為我不止一次接到宿舍區的某一位養狗教授的電話,抗議我英氣卓倫之力古(但從他嘴裡說出就成了:「你家那隻兇狗」),與他豢養的那個肉頭在路上大聲說話(即,「對著我家的狗猛吠」),並責我以公民應有之文明(翻成白話即,「你該把他綁起來」)。類似這種對狗與狗之事的人類介入,後來還有好幾樁,最終逼得我不得不圈住力古。從此,對人友善,對同類好奇,原則上不首先使用暴力的力古,失去了自由。而竹麥呢,反是因為個兒小,無威脅之外型,在宿舍區裡自由自在,愛去哪兒去哪兒。力古於是成為了我宅之司閽大聖;神雖王,不善也。他是會對所有意欲接近的人吠,但只要你敢繼續接近他、表態要交朋友,他就立馬成為你的朋友。瞧那個友善勁兒,哼!力古不勢利;送報伕、郵差、拾荒者,與教授,一視同仁。年,朋友賀照田也在山上,夏夜,常拎著幾杯仙草芋圓到戶,我總是先聽到力古唱,然後是照田答:「嗨,力古道,你好」──以北人南相所特有的溫柔北方腔。 力古野性未褪,能做朋友,能做戰友,但不能當寵物,他喜歡人的溫情,但不習慣人的溫情表達方式;他不讓你好好摸、好好抱,他總是要反抱你,反撲你,他總是扭啊扭的,讓你摸不定、抱不住。我自小喜聞狗毛味,竊以為天下一大香澤,但大方的力古卻總是小氣地扭啊轉啊晃啊,我硬是貼不近他的頭。能聞到的少數幾次都是趁他睡覺偷聞來的,但即便如此,機會也很少,因為他很警醒,睡得很淺,一點兒動靜就醒。我們都認為他不如竹麥好命,人家竹麥可是睡得昏天暗地,滿嘴哈拉子。莊子說過,山木以不才得終其天年。 力古老是醒著,好像人生太短,不醒著不划算一樣。而任何有生跡象,只要來到力古的管轄範圍內,他馬上進入一級戒備。早上,我們在他旁邊看過死的老鼠,傍晚,我們在他旁邊看過死的小鳥,也看過死的小蛇──眼鏡蛇。 力古開始跟眼鏡蛇過不去,也是有個過程的。 初,力古與竹麥是與借路而過的眼鏡蛇相互戒備、依禮而行的;眼鏡蛇無害通過,他們低吠目送──中隔一適當距離,有點像今天的南海局勢。他們倆的態度那可真是臨深履薄啊。直到那時,我才真正瞭解基因之偉大。他們倆從小離開父母兄長,離開了一切可以手把著手傳授經驗與功夫的長輩,帶著一身乳毛來到島嶼西部的大肚山,啥也沒學過,但怎麼就知道這個會昂首吐信的、脖子會變成一個大飯匙的傢伙,是不好惹的壞東西呢!在他們那兒有一縵縵深深的恐懼,這你從他們的叫聲就聽得出來,以至於,當我們在屋裡聽到力古以如此音頻發聲時,我們就知道蛇來也。我家門前正好是一條眼鏡蛇公路,沒法兒。 有一天夜裡,力古又搖警報器了,那個聲音溢著憤怒滲著恐懼。為了壯膽,我順手拎了一根棍子出去。結果啥也沒看到,我說:行了,力古,別神經了。但他還是對著水缸花盆猛叫,好像按照他的美學觀這兒不該擺設水缸花盆這種靜物似的。我拿著小手電,用棍子輕輕撥著各個角落,突然間,在青白的光線中,乍現一條煞白蛇頭,銀白的麟甲上鑲著細細的兩條眼,與一根又像花蕊又像閃電的吞吐蛇信,我頓時急了,照著就打。說也奇了,力古這時連祖訓也擺一邊,唰地一個箭步欺上蛇身,不學而成、不慮而得,咬住蛇的三寸,然後讓他的南瓜頭將欲左之必先右之,猛然使個太極甩頭,讓冰涼的蛇身擦過我夏天赤裸的臂膀,一線飛向草地,然後,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,估計是脫臼了,或──暈了。此時,消防隊的老兄們才嘈雜迆邐而至。力古是真生氣了,對著蛇罵個不停,罵到滿嘴都是白沫,我估計那大概是揉雜了憤怒、恐懼、興奮與榮譽,各種心情吧!是夜,為力古道慶功,大度山宴開一罐頭。 於是,我明白了為什麼宿舍區裡慘遭蛇吻的狗都是那種大洋狗。在他們的基因裡沒有輸入「眼鏡蛇」這個符號,所以渾然不當回事,以致於常有人第二天早上起來看到他的大狗早已身僵多時,身旁錯落幾段血肉蛇身。我也忽然明白,力古道進退取予都是依古道而行。他獨自時,戒慎恐懼,有所不為,所謂「慎獨」者也,但是,一旦他心目中的好友展開攻勢,對方與己方呈現戰爭格局時,力古就是一個死士,忘我地投入戰場,為了基因榮譽,也為了伙伴安危,竟不知安危為何物。《聊齋》卷一有一個叫「葉生」的感人故事,說這個姓葉的讀書人,「魂從知己,竟忘死耶」,力古又何嘗不是如此呢?在他的黑白圖像記憶深處,在白雲千載的中央山脈的層谷疊巒裡,他的祖輩與牠們的獵人同志正是如此地同進同退,不曾稍懼於那些比他們體型更龐大、手段更毒辣的對手,不管是野豬帝國主義、黑熊帝國主義,或是眼鏡蛇帝國主義。在這一點上,卑南族的力古與卑南族的頭目是一致的,頭目哈古曾不乏驕傲地對我說:「大有什麼用,我們是小辣椒啊!」有回,力古碰到入侵我院,把我院當公海的一隻德國大狼犬,迅即亮出他如惡魔般的森森白牙,紅黑色內唇翻皮上頂,把鼻子都幾乎蓋過去,那張臉呦,像極了一隻剛從地獄放出來的兇惡大蝙蝠,不談判、不商議,直接跳上大狼狗身上,鎖咬住脖子,大狼狗當場軟了,聽由力古拖著牠。那次把我急的,猛敲力古的頭,大聲說:鬆口、你鬆口啊。 然而,慶功罐頭到底是開壞了,因為那形成了一個錯誤暗示。之後,力古戰術激進化,開始主動攻擊經過的蛇了──而這是為何我們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小蛇的緣故。力古低頭看看地上的小蛇,抬頭看看我。那意思清楚不過,但我知道不能再誤導他了。大蛇無盡,而力古終究會老,以老狗而犯大蛇,殆矣。我不能想像力古如何老,但他一定會老,我為他擔憂,一如為一個勇士擔憂。想像一個齒牙動搖,視茫茫,耳昏昏的老戰士,遭到那些名叫鎮關西、鎮關東之類的市井潑皮的戲弄……。 去年此時,力古不吃不喝,也不想動。接連好幾天,冬陽明媚,我把套在力古脖子上的鍊子解開,讓他自己去找點草藥吃。他腸胃不適時,自己會去找些草葉來吃,其中最喜歡的就是馬櫻丹葉子,他一葉葉地咬下來,有時候咬不下來,就用嘴扽下來,那時候,我就等著他,而站在那兒等力古的我曾這麼覺得,如果抽煙未嘗不失為一件美事的話,那只會是在黃昏時我悠然地等力古吃馬櫻丹的時候。他要吃三四十片,然後在大約三五分鐘內,讓腹部激烈收縮運動,然後把所吃的草葉挾著一大堆黏稠液體,給嘔吐出來,然後,無比歡快。這次,我放他,他卻哪兒也不去了,選擇在我們院子對面的一個高高地方,孤寂地往巷口方向看。那兒是他的未來嗎?還是他仍有所等待?那幾天我都有課,上課前帶點麵包或是餅乾之類的餵他吃點。讓我難過的是,以前沒底的肚子,如今僅為交情故,勉強吃個兩口,就緩緩地把頭擺過去了。 力古走得很快。走的前兩天,我再度看到一種黑灰色籠罩在他身上。上一次他臨上那個顏色時,是他年輕時以欲望的形式執行生命所傳遞的義務時,那,於他,也是生死之際的事啊,這一次,則是他面對真正的終點之時。在生、死、情愛的大祕密上,人和狗是多麼的相近啊,而狗似乎比人還堪得透。民吾同胞,物吾與啊! 力古走的那天我在台北,清晨,我接到電話那邊傳來的哭泣聲,她說,「力古走了。」我怔了半天,發了個短信,打了個電話,電話那邊是我住大學宿舍的大女兒,她沉默兩秒鐘,然後哇的一聲大哭起來,把同屋的室友全驚醒了,小女生們都下了床安慰她。這是女兒頭一次撞到生命的無常,既是為力古而哭,也是為生命的祕密而哭。我則是欲哭而無淚,悲夫。 力古走得好,走在最有尊嚴的時候,算算,他虛歲也十二了。我們都不曾打算送他去獸醫那兒。我們把他埋葬在我們的後院,在同樣是從台東來的椰子樹下,他長眠了。據說,這是違反宿舍區規定的,寵物屍體要交由專業單位火化,云云。但我們從來不把力古視為寵物,他是一個戰士,生於台東中央山脈,死於台中東海大度山。然而,他也是一個不曾犯過罪的囚犯;我們為了文明秩序,犧牲了他的性愛自然。 再幾天就是力古的週年。這一年來我常憶及力古,前兩天去力古故鄉參加豐年祭回台中之後,更是頻頻想到他,估計和那兩天看到了一樣的太平洋、一樣的藍天白雲,一樣的青色山脈,以及老邁些了的頭目、頭目娘,與族人長老,而若有所思,可能有關吧。好在下著這場夜雨,我們可以在爐子上燒壺熱水,雙手捧著碗熱茶,慢慢說些力古的事…… 趙剛 /1/3於大度山 pourmarx扫我~扫我~扫我~赞赏 人赞赏 复方木尼孜其颗粒作用是什么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郑华国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aiwanzx.com/twys/830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台湾地区大法官提名人支持同性婚姻
- 下一篇文章: 图文新闻台湾联合报大陆新发现采访